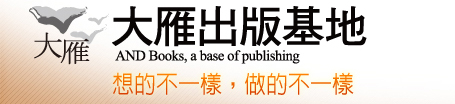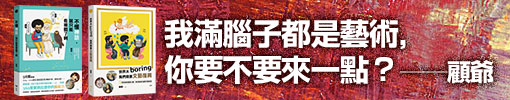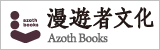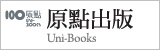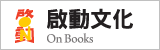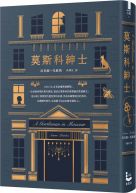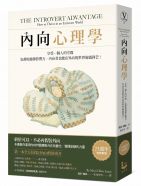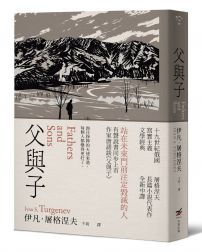<作家與作品>
站在未來門前注定毀滅的人:讀屠格涅夫《父與子》(節錄)
為什麼讀《父與子》?我想,應該是到了(重)讀這部太熱騰騰小說的時候了──尤其,如果你有些年紀了,不再那麼輕易被騙、被唬住被煽惑,不是只會用激情看世界;或,如果你小說閱讀已達一定的量,不會太大驚小怪了,我心沉靜,有餘裕可以看較細膩流動的部分。
其一
書寫屠格涅夫,溫和的文學巨人(成就,也是體型),我們先放一段他的話在這裡,出自他另一部小說《煙》:「我忠於歐洲,說精確點,我忠於……文明……這個字既純潔而且神聖,其他字眼如『人民』……或者『光榮』,都有血腥味。」
我無比無比同意。這番話,很清楚講出了屠格涅夫的價值選擇及其深深憂慮,他太靈敏的嗅覺(一種很容易給自己帶來危險的能力)早早就聞出彼時還沒那麼明顯的鮮血氣味。今天,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堆下來,我們知道屠格涅夫是對的。屠格涅夫一直是比較對的那個人,只是當時人們不夠相信他、不太願意相信他而已,他極可能是整個舊俄時代最被低估的人。
不要向歷史討公正,我們能做的只是,竭盡所能讓人類歷史可以稍稍公正一些。
是這個最溫和不爭(或柔弱不敢爭)的人,而不是性格強悍見解激烈的托爾斯泰或杜斯妥也夫斯基,寫出了這部十九世紀舊俄(也許就是人類小說的第一盛世)最爭議的小說。說稍微誇張一點,《父與子》是炸彈,當場把一整個俄羅斯老帝國炸成兩半,當然,傷得最重的必定是引爆者屠格涅夫自己。
時間點是這樣,時間總是最重要──《父與子》寫成於一八六二年,小說裡的時間則是一八五九年(所以《父與子》是當下的、即時的書寫)。這裡有個巨大無匹的時間參照點:一八四八,人類革命歷史不會被忘掉的關鍵一年。
我們稍稍花點工夫來談一下,畢竟這是應該要知道的──一八四八,近代革命史第一震央的巴黎爆發了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並迅速席捲整個歐洲,於此,歐洲統治者中反應最快的反而是俄皇尼古拉一世,他立刻出兵蕩平波蘭如築牆,把革命浪頭成功擋在西邊,並回頭解散莫斯科大學如拔除禍根,高壓統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強度。往後七年,整個俄羅斯呈現全然的噤聲狀態,這就是著名的「七年長夜」,「活在當時的人都以為這條黯黑甬道是不會有盡頭的……」(赫爾岑)。《父與子》小說一開始,苦盼兒子阿爾卡季回家的老好人尼古拉・彼得洛維奇陷入回憶,想起來的便是──「然而繼之而來的是一八四八年,有什麼辦法呢?他只得返回鄉間。他很長一段時間都意志消沉、無所事事,遂關心起田地改革……」
雪上加霜,俄羅斯良心、心志最堅韌、最直言不屈的別林斯基就在一八四八年病逝,別林斯基也是屠格涅夫最尊敬的人,別林斯基大七歲,亦師亦友。《父與子》小說裡,這對結伴而行年輕人阿爾卡季和巴扎洛夫的關係樣式差不多就是如此,屠格涅夫書寫時有沒有記起別林斯基呢?我相信,日後這三十年(屠格涅夫單獨活到一八八一年)他必定不斷想起他這位光輝、無畏的朋友,在他需要做決定尤其需要勇氣時如一靈守護,諸如此類時刻終屠格涅夫一生還挺多的。
又,最聰明且筆最利、批判幅度最大的赫爾岑亦於一八四七年去國流亡。扛得住壓力的人不在,當時,整個俄國確實有瞬間空掉的感覺。
一八四八,歷史地標一樣的數字,已在在確認,這是革命戲劇性切換的一年,從遍地花開到歸於沉寂,再在這一年──西歐這邊:沸沸揚揚百年的歐洲革命到此終結,這一頁歷史翻過去了,西歐轉向另一種前進方式,年輕人覺得較不耐較不過癮的方式;俄羅斯這邊:革命從此東移,新核心是俄羅斯,儘管一開始並不像,俄羅斯的當下景況無疑更沒生氣更沒空間可言,沙皇、東正教和農奴制這著名的三位一體鐵桶般牢牢罩住整個俄國,但這是壓力鍋啊,無處去的能量不斷的集中、堆疊、加熱,歷史結局,當然是炸開來撼動全世界且成為下一波革命輸出中心的紅色革命。
《父與子》的狂暴主人巴扎洛夫,日後被說成是「第一個布爾什維克」,小說被推上這種政治高位,當然是文學的不幸。
一部小說就把一個國家一分為二,必定是原本就有著夠大夠深的裂縫存在,如地殼斷層那樣,《父與子》恰恰好炸中要害──俄羅斯這個非歐非亞、又歐又亞,如冰封如永晝的沉鬱帝國,其實是領先「西化」、「歐化」的國家,啟動於彼得大帝一個人的獨斷眼光。彼得大帝毅然把國都推進到極西之境,於芬蘭灣涅瓦河口的沼澤地硬生生打造出新國都,這就是聖彼得堡,一扇門,一個採光窗口,一隻「看向西方的不寐眼睛」。普希金的不朽長詩《青銅騎士》,寫的正是聖彼得堡加得大帝,凝聚為這座青銅鑄的躍馬騎士像:「那裡在寥廓的海波之旁/他站在充滿偉大的思想/河水廣闊地奔流/獨木船在波濤上搖盪/……而他想著/我們就要從這裡威脅瑞典/在這裡就要建立起城堡/使傲慢的鄰邦感到難堪/大自然在這裡設好了窗口/我們打開它便通往歐洲」。
談西化我們常忘了俄國,忘了這一有意思又極獨特的歷史經驗。不同於日後西化的國家,俄羅斯完全是自發的、進取的,並非受迫於船堅炮利如中國如日本,因此原來沒屈辱沒傷害,西化是相當純粹的啟蒙學習之旅,充滿善意和希望,是文明的而非國族的,也就和對俄羅斯母國的情感沒有矛盾更不必二選一。可也正因為這樣,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的西化其實僅及於薄薄一層上階層的人、貴族世家有錢有閒有門路的人。以撒・柏林指出來,這些西化之士是各自孤立的啟蒙人物,只要是文明進步事物無不關懷,大而疏擴,且只停留於思維和言論的層面。
這就是一八四八之前俄羅斯奇特的上下截然二分景觀──為數很有限但熱情洋溢的歐化知識分子,和底層動也不動如無歲月無時間的廣大農民農奴。別林斯基如此說:「人民覺得他需要的是馬鈴薯,而不是一部憲法。」
來自西歐的傷害遲至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的揮軍入侵。這場大戰,俄方靠著領土的驚人縱深和冰封漫長的冬季「慘勝」。但儘管滿目瘡痍,俄國上層的西化之士心思卻極曖昧極複雜,因為這是法蘭西啊,這是第一共和之子拿破崙、是自由平等博愛云云法國大革命這波人類進步思潮的光輝成果及其象徵,所以,這究竟算侵略還是解放?是壯闊歷史浪潮的終於到來?畢竟,有諸多價值、心志乃至於情感是恢宏的、人共有的、超越國族的(彼時民族國家意識才待抬頭)。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小說中,我們讀到,即便戰火方熾,俄國貴族的宴會舞會(照跑照跳)裡代表進步、教養或至少時髦交談的語言仍是法語,甚至還對拿破崙不改親愛不改暱稱(依今日用語,可譯為「破崙寶貝」)。唯家家悲劇遍地死人這是基本事實,平民也永遠是戰爭最大最無畏的受害者。這場戰爭於是帶來大裂解:其一發生在西歐與俄國之間,歷史總會來到人無處可躲閃得二選一的痛苦不堪時刻(葛林講的,你遲早要選一邊站的,如果你還想當個人的話);另一發生在上層歐化知識分子和一般平民之間,之前只是平靜的隔離,如今滿蓄能量如山雨欲來,開始滋生著懷疑乃至於仇恨。
最後決定性的一擊就是一八四八了,其核心是絕望,雙重的絕望──對歐洲絕望:革命不復,進步思潮全線潰散,西歐那些天神也似的人物(如馬志尼)一個個逃亡到大洋上的倫敦彷彿偌大歐陸已無立足之地,西歐自顧不暇至少已不再是答案了,俄國必須自己重找出路;更深的絕望則指向這一整代歐化知識分子,別林斯基已死,赫爾岑遠颺,巴枯甯被捕,所有華麗的、雄辯的、高遠如好夢的滔滔議論一夕間消失。比起單純噤聲更讓人不能忍受的是變節,其中最駭人的當然是巴枯甯那份聲名狼藉的<自白>(一八五一),他在獄中上給沙皇,滿紙卑屈求恕之語,這所有一切原來如此一戳即破,沒用,還敗德。
一八五六年,七載長夜之末,屠格涅夫先寫出了《羅亭》(很建議和《父與子》一併讀),對屠格涅夫這樣一個徹底歐化一生不退的自由主義者而言,這當然是一部最悲傷的小說。羅亭這個人物據悉是依巴枯甯寫成的,但其實就是他們這一代人、是相當相當成分的屠格涅夫自己。抱怨《父與子》對下一代年輕人不公正的人尤其應該也讀《羅亭》,他寫羅亭比寫巴扎洛夫下手要重,狠太多了,彷彿打開始就設定要暴現他嘲笑他(自己)──羅亭是那種春風吹過也似的人物,彷彿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議論,而且再冷的話題由他來說都好聽有熱度,如詩如好夢如福音。但屠格涅夫真正要讓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人、這些個議題撞上現實世界鐵板的狼狽模樣。那是一連荒唐的失敗,甚至在失敗到來之前人就先怯懦地逃了,農業開發不行,挖運河不行,連談個真實戀愛都不行。羅亭一事無成,只時間徒然流去,只人急遽的老衰。
屠格涅夫對羅亭僅有的溫柔是,幾年後他多補寫了一小段結尾如贈禮,給了羅亭一個體面的、巴枯甯理當如此卻無法做到的退場──時間正是一八四八,地點是革命風起但又敗象畢露的巴黎街壘,一身華髮的、身披破舊大衣的瘦削男子,以他尖利的嗓音要大家衝,但子彈擊中了他,他跪下去,「像破布袋般臉朝下撲倒」。
一八四八之後,已中年了、或初老的這一代羅亭,由此有了個很不怎樣的新名字,如秋扇如見捐的冬衣,叫「多餘的人」。
《父與子》這部命名就以一分為二的小說,於是這麼一刀兩半──西化人士和斯拉夫民族主義者,自由派和民粹派,溫和派和激進派,改革者和革命者。以及,應該是最根本的也最難真正消弭的,因為有生物性基礎:中老年人和年輕人。
這個二分歷史大浪一路衝進二十世紀的紅色革命之後依然其勢不衰(蘇聯的統治是一長段不斷二分不斷清算的歷史,當然是由理念差異轉向全力傾軋,但人類歷史也少見這麼溯及既往、報復心如此重的政權)。所以說,《父與子》即便到了二十世紀也很少被好好讀,或說,一直被奇奇怪怪的讀──極仔細極挑眼,凶案現場鑑識那樣不放過任何一字一句的可利用線索;同時又最粗魯最草率,但凡無法構成罪證或用為攻擊武器就一眼掃過,或更糟糕,誇大的、扭曲的、隨便的解釋。這真是一部不幸的小說。
說現在應該是好好來讀《父與子》的時候,並不是說此一二分法浪潮已然止息,我們等不到這樣的時日,人類歷史也永遠沒這樣的時日,我們活在一個動輒二分且二律背反的世界,人那種不用腦的激情也源源不絕,這就是人,「人真是悲哀啊」(美空雲雀)。但勉強從好的一面來說,這也是文學的力量吧,一部厲害的作品,總會深深觸到人很根本的東西,幾乎是永恆的東西,好作品總生風生浪。比方,中老年人和年輕人的二分,事實上,今天的「年紀戰爭」或「憎恨老人」顯然比屠格涅夫當時更熾烈更普遍,也更反智放肆,所以,應該還沒到歷史最高點對吧。
世界冷差不多就可以了,剩下的得我們自己來──保持心思清明,並努力讓他成為一種習慣,慢慢的,他會熟成為一種能力。
「我們有義務成為另一種人。」(波赫士)……
──本文轉載自《我播種黃金》唐諾/2023印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