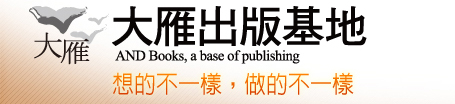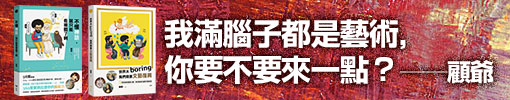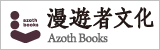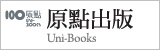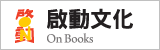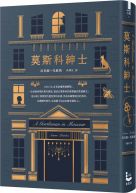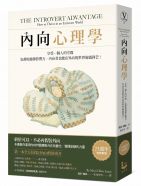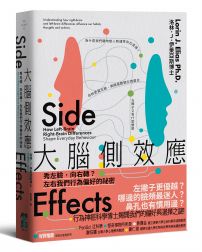|
|
|
|
|
|
|
|
 |
切換至電子書 |
 |
| 大腦側效應:秀左臉,向右轉?左右我們行為偏好的祕密 |
| Side Effects: How Left-Brain Right-Brain Differences Shape Everyday Behaviour |
|
| 分類:
自然科普 |
| 書號:
NM0012 |
| 作者:
洛林.J.伊萊亞斯博士 |
| 原文作者:
LORIN J. ELIAS, PH.D. |
| 譯者:
吳煒聲 |
| 出版社:
啟動 |
| 書系:
On Mind |
| 出版日期:
2025-08-27 |
| 語言:繁體中文
ISBN:
9789864932191
|
| 規格:
14.8 cm * 21 cm / 平裝 / 黑色 |
|
頁數: 336 頁
|
| 定價:
550 元 |
| 關鍵字:
行為科學 人類行為 行為認知 神經科學 行為模式 感知 行為心理學 側偏好 側偏向 大腦認知 行為神經科學 |
|
|
|
|
|
|
| 內容簡介 |
 |
|
|
|
|
|
為什麼我們親吻戀人時通常向右歪頭?
自拍愛露左臉、媽媽喜歡朝左抱嬰兒?
左撇子又有什麼優勢?
我們的身體看似完美對稱,
行為卻隱藏著令人驚訝的左右失衡!
從慣用左手或右手,到眼、耳、鼻孔⋯⋯
甚至語言和文化中,都內嵌著左右偏好。
行為神經科學博士將揭開你的偏好與選擇之謎,
提供接吻、擺姿、選機位的有效建議(?)
探索這有趣又神祕的側邊效應(○)
人類的行為是不平衡的。約90%的人慣用右手,這種偏好已持續數十個世紀,而且似乎是人類特有的現象。抱著新生兒時,多數人都習慣將嬰兒抱在左側。擺姿勢拍照時,我們傾向於將左臉頰朝前……
從日常動作到重大決定,每個行爲背後都隱藏著側偏好。我們的行為為何如此不平衡,又和我們的大腦有什麼關係?人類如何本能地利用這些資訊,使我們的形象更具吸引力和影響力?
研究左右腦差異逾二十年的洛林.伊萊亞斯博士,解讀藏在大腦中的祕密,帶我們發現這些偏向與偏見如何影響人類的行為:
與戀人接吻時,我們的頭為何自然地向右歪斜?而親子之吻卻沒有這種偏好?
抱著嬰兒或毛小孩時,為什麼大部分人習慣抱在左側?
運動員刻意練習左手,例如納達爾,因為左撇子在體育競賽中比較有利?
從左側打光的物體比較好看?藝術、廣告如何利用人們的光源偏好?
語言中也有左右偏見?為什麼描述左傾事物比較消極,甚至帶有貶義?
作者引用大量的科學研究、歷史紀錄和跨文化比較支持其論點,證明「側效應」是大腦功能側偏化的廣泛體現。有助我們理解自己、解讀他人的行為,並加以應用於複雜的社交互動和藝術創作等領域,發現潛藏在行為表象中的無限可能。
|
|
|
|
| 名人推薦 |
 |
|
|
|
|
|
好評推薦
PanSci 泛科學
怪奇事物所所長
焦傳金(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特聘教授)
謝伯讓(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謝仁俊(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終身講座教授)
(依姓氏筆畫排序) |
|
|
|
| 作者簡介 |
 |
|
|
|
|
|
作者簡介
洛林.J.伊萊亞斯博士(LORIN J. ELIAS, PH.D.)
薩克其萬大學(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屢獲殊榮的心理學教授兼學術副院長。他取得了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行為神經科學(behavioural neuroscience)博士學位,25年來一直研究左腦和右腦的差異。他的聯邦資助研究計畫已經發表超過70篇研究論文,分別刊登於《神經外科》(Neurosurgery)、《神經心理學》(Neuropsychologia)、《皮質》(Cortex)、《大腦與認知》(Brain and Cognition)、《側向性》(Laterality)、《認知大腦研究》(Cognitive Brain Research)和《行為神經科學》(Behavioural Neuroscience)等期刊上。
這些研究已被世界各地的主流報章雜誌廣為報導,例如《柯夢波丹》(Cosmopolitan)、《連線》(Wired)、《美信》(Maxim)、《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和《紐西蘭先驅報》(New Zealand Herald)。伊萊亞斯博士不僅成就斐然,更是名聞遐邇的心理學教授,也在薩克其萬大學獲得諸多教學獎項,其中包括名師獎(Master Teacher Award)。他將看似複雜的主題和深奧的內容變得通俗易懂、引人入勝,甚至新奇有趣,從而贏得過人的聲譽。
譯者簡介
吳煒聲
美國蒙特瑞國際研究學院中英口筆譯組碩士,目前任教於陽交大學,致力於英語教學與中英翻譯研究。 |
|
|
|
| 目錄 |
 |
|
|
|
|
|
序言
第1章 慣用手:左撇子更優越嗎?
第2章 腳、眼、耳、鼻:從「右」開始,就對了
第3章 語言暗示:左側遭到歧視了
第4章 左親親、右親親:我們會接吻嗎?
第5章 抱抱偏見:你抱娃娃的方式對嗎?
第6章 擺姿勢:秀出最迷人的半邊臉頰
第7章 光源偏好:我們調對燈光了嗎?
第8章 藝術、美學和建築中的側偏好
第9章 慣用手勢:遺留的行為化石
第10章 轉向偏好:右轉、右旋、右繞圈
第11章 座位偏好:選不選2B座位?
第12章 運動偏好:左動作「對決」右動作
後記
致謝
資料來源 |
|
|
|
| 序 |
 |
|
|
|
|
|
後記(節錄)
我們總是認為副作用(side effect,與本書討論的側效應為相同的英文詞組)是個壞事。抑制打噴嚏和鼻塞的抗過敏藥物,可能會讓我們昏昏欲睡。除非我們在睡前服用,否則這種副作用沒有什麼好處,甚至可能讓我們根本不願意服用。在一些罕見和特殊情況下,副作用也可能有好處。舉例來說,女性服用口服避孕藥防止意外懷孕,但這些藥物可以避免長粉刺。阿斯匹靈通常當作止痛藥,但它還有助於預防心臟病和中風,甚至可以提高結腸癌或攝護腺癌的存活率。敏諾西代(Minoxidil)最初是為了治療高血壓而開發,但現在可以局部塗抹治療雄性禿。⋯⋯
這本書顯然不是在討論藥物的利弊,但某些原則同樣適用於我們功能失衡的大腦所產生的側效應。這些影響很容易觀察到,但其意義不僅是用來滿足人們對科學的好奇心,或者只是瑣事一件,無足掛齒。當我們逐漸了解這些側效應,反而應該藉此改善自己用於社群媒體的圖片、約會軟體的個人檔案、挑選座位的想法,甚至廣告活動的圖像設計。
我每一章只討論一種側效應,將其條理封裝在專屬章節內,但這樣的安排內容會有一個缺點──讀者可能覺得本書探討的側偏好完全是相互獨立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慣用手是最明顯的側偏好,它會影響但通常不會導致其他側偏好,例如抱姿側偏好或者慣用眼、慣用耳或慣用腳。然而,某些側偏好偶爾可能導致另一種側偏好。例如,體育運動中的許多側偏好都是由選手的慣用手所造成。此外,其他側偏好也會相互作用。我們的右轉偏好可能會與情人接吻時偏好向右歪頭。我們擺姿勢時傾向露出左臉頰,可能與我們對左側照明的偏好相互作用。換句話說,我深入描述的十幾種側效應大多是獨立陳述的,但它們並非總是單獨呈現。
人類最明顯的失衡行為是用手習慣。我們分析過洞穴壁畫等古代藝術,從中得知在五十多個世紀以來,90%的人類都是右撇子,並且不存在左撇子主導的文化。慣用右手似乎也是人類獨有的特徵。如果大猩猩和猴子也有側偏好的話,牠們似乎偏愛使用左手,而貓和狗等動物不像偏愛右手的人類,會表現出物種層面的「用爪偏好」。此外,我們也會頌揚「右」(在英語中,「右」和「正確」是同一詞right),卻用險惡(sinister)或粗俗(gauche)等話語妖魔化「左」。左撇子會在家族中遺傳,並且會談及許多美好的事物(如左撇子智商很高、有藝術和音樂天賦、非常擅長數學)。然而,左撇子也與許多不好的事情有關(好比自體免疫疾病、出生壓力、思覺失調症、閱讀障礙)。當今社會中年輕人的左撇子比例較高,而老年人的左撇子占比較低,因此人們很容易得出以下結論:左撇子沒有右撇子活得長。然而,社會壓力等因素至少是讓這兩批人壽命有所差異的原因。
除了慣用手,我們對腳、耳朵和眼睛也有強烈的側偏好。與慣用手不同,我們其他側偏好對於不經意的旁人來說不太明顯,這也使得這些側偏好不易受到社會壓力的影響。許多文化都有嚴格的規定,哪隻手應該用來準備和抓取食物(右手),哪隻手應該用來清潔自己(左手)。然而,慣用腳、慣用眼和慣用耳可以在更少的社會干擾下發展,因此我們更能以它們當作線索,從中了解某個人獨特的大腦偏側化。儘管文化對我們慣用腳、慣用眼和慣用耳的影響不太普遍,但多數物品仍然是為「右側主導」的世界所製造,包括步槍準心或顯微鏡的瞄準鏡。
有些人很難區分左右,一旦犯錯,後果可大可小,輕微的只是讓人惱怒,嚴重的卻足以致命。例如,開車時轉錯方向可能會出人命,動手術時搞錯左右邊也可能出大事。當我們使用同一組簡單的語詞描述左右時,就會出現這些錯誤。然而,一旦考慮到用於描述左和右的各種語詞時,事情可能會變得更加混亂。在這些字語中,許多都帶有價值判斷,與「右」相關的詞常蘊含正面意涵(正直、正確、準確、真實、乾淨),而「左」則被貶低,牽涉更多的負面聯想(彎曲、錯誤、笨拙、虛假、骯髒)。我們用來區分左右的字詞也被納入政治語言,這些源於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國民制憲議會的席位安排。
接吻在流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關於接吻的科學研究卻非常罕見。然而,近期的研究開始揭露不同類型的親吻(與情人的接吻、親子之吻、社交場合問候式親吻)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表達。情侶接吻時傾向於向右歪頭。然而,當父母親吻孩子時,這種側偏好就消失了。同理,如果兩個完全陌生的人接吻,因為雙方都不熟悉彼此,這種陌生感便會消除右傾偏好。在社交問候式親吻中(這在歐洲很常見),多數地區表現出右傾偏好,但世界上的某些地區卻表現出左傾偏好。總體而言,這項研究指出,人們和情人接吻時,通常會將頭轉向右側,但親吻父母或孩子時,會將頭擺正、甚至轉向左側親吻的情況很常見。當你前往歐洲旅行時,應該查查資料,看看第一次與某人見面時應該親吻多少次,以及該親吻哪一側的臉頰。⋯⋯
轉頭是另一個顯示側效應的日常動作。把頭向右轉的傾向是人類最早的一種失衡行為。母體懷孕38週後,我們便可從胎兒身上清楚看見這點,而這比文化或社會學習對孩子的影響要早得多。這種側偏好會貫穿人的一生。如果我們叫某個成人走過空蕩蕩的走廊,再轉身返回原路,這個人很可能會向右轉。當人們開車、進入商店、運動,甚至跳舞時,我們都能看到這種右側偏好的證據。多數古代舞蹈都有轉圈動作,無不傾向於順時針(向右)旋轉。
當人們進入房間並選擇座位時,我們也可以觀察到轉向偏好,但這個現象比較複雜,不僅是決定轉向哪個方向的問題。什麼會影響人們走進教室或電影院時如何挑選座位?人們選擇大型音樂會或越洋航班的座位時又會如何?我們選擇坐在哪一側,取決於自己期望的體驗類型以及大腦的側偏好。由於右腦主導情感處理,而從左側載入訊息主要由右腦處理,因此我們預期人們更喜歡從左側感知情感內容。看看電影院的座位偏好,就會發現這一點。相反地,左腦通常在語言處理方面占主導地位,所以我們傾向於從空間右側感知語言。看看教室的座位偏好,就會發現這一點。人們喜歡坐在電影院的右側和教室的左側。我們從座位選擇看到的側偏好取決於人們期望看到什麼。
從其他形式的娛樂活動(例如觀看體育比賽)也很容易觀察到側效應。側偏好(例如打棒球時的慣用手),顯然在業餘和職業運動選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透露側偏好的最佳紀錄來自運動界。然而,人的側偏好甚至會影響看運動比賽的觀眾,決定足球進球漂不漂亮,或者拳擊比賽中某一拳的力道強不強。從左到右閱讀者,往往更喜歡觀看從左到右的動作。我們會誤判速度和距離,這點也會影響選手在賽場上的表現。人們傾向認為空間左側的物體比右側物體更近、更大。
這本書的誕生(或至少是構想)可以追溯到2004年,我從蒙特婁(Montreal)參加完一場研討會、搭機返家途中。我當時剛開始探索光照側偏好,並向研究抱姿和擺姿側偏好的同事展示了些許成果。離開蒙特婁時,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側偏好可能如何相互作用且彼此影響,隨即在9,000公尺的高空為本書勾勒出粗略的輪廓。也許當時機上空氣稀薄,或者我剛結束一場精彩的會議,所以睡眠不足,因此在那次回程中寫下的章節大綱只有部分可行。話雖如此,即使我當時全心撰寫大綱,我也不認為能夠寫出完全可用的內容。從那時起,許多探討側效應的新文章在後續數年裡陸續浮上檯面。從那時起,甚至出現了專注於這些問題的研究團隊,而這個領域令人興奮和具有影響力的嶄新研究,也比以往更快問世。到了最後,這類研究文獻數量充足、品質上乘和內容一致連貫,讓我得以紮紮實實寫出本書。出版這樣的一本書,既讓我興奮,也令我恐懼,因為我知道筆頭的墨水一乾,又會出現另一項需要納入本書的偉大新研究。在我撰寫本書時,不得不忍痛擱置一些章節(像是〈交通運輸的側效應:汽車、飛機、船隻和火車〉﹝Side Effects in Transportation: Cars, Planes, Boats, and Trains﹞,以及〈從右翼到左翼:政壇的側偏好〉﹝Right Wings to the Left: Side Biases in Politics﹞),因為這些領域的研究才剛開始起步。如果運氣好的話,本書的續集和(或)更新版,將在18年內問世。 |
|
|
|
|
|
序言(節錄)
人類行為是傾向一側的。我們的身體是對稱的,至少外觀上如此,但我們的行為卻不是這樣。左右手看起來區別不大,但幾乎90%的人慣用右手寫字和丟東西,從事技巧性活動時,也會經常使用右手。然而,多數人抱嬰兒時,通常會將其抱在左側。一般人擺姿勢讓別人畫肖像或拍照時,無論是16世紀的繪畫或者IG自拍照,都習慣露出左臉頰。而我們親吻愛人時,經常將頭向右歪斜。為何我們的行為會如此左右不對稱?我們又如何從這些現象去理解大腦呢?當我們將自拍照上傳到約會網站的個人簡介時,該如何運用這些資訊讓我們的自拍照得更好看?或者,我們該如何使用Photoshop處理政治廣告,讓候選人更能吸引某些選民?了解左右腦差異如何改變我們的觀點、傾向和態度,可以幫助我們在藝術、建築、廣告甚至運動方面,表現得更好嗎?讀完本書後,你將會了解大腦的側偏向(lateral bias)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行為,以及該如何善用這些資訊讓自己表現得更好。
在科學實驗室、醫院的腦部掃描儀上,或者從有單側腦損傷或進行腦部手術後的個人行為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左右腦的功能差異。然而,我們從正常人的日常生活中也能輕易觀察到這類左右差異。人的失衡行為就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
我們的某些左右差異非常一致,而且由來已久。例如,無論男性或女性,無論來自馬來西亞或法國,90%的人都喜歡用右手。此外,根據對古代文物和藝術品的分析,人類這個物種在五十多個世紀裡一直偏好使用右手。其他強烈的側偏好(lateral preference)是近世才出現,只有數百年的歷史,好比肖像畫中擺姿勢的偏好。如果仔細觀察描繪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宗教藝術作品,便會發現在90%的畫作中,耶穌都是向右轉頭,露出左臉。我們抱嬰兒時的側向姿勢偏好也由來已久,但遠遠沒有像我們在群體層面上慣用右手的強烈偏好,大約70%的人抱嬰兒時都是抱在左側。
本書檢視的不平衡行為與我們潛在的左右腦差異有關。每個人的大腦都是獨一無二的。雖然每個人的臉龐外觀各不相同,但多數人的頭骨內都有相同的構造,具有同樣的整體形狀、位置和功能。然而,每個大腦卻是不一樣的。本書分析的左右差異都是「基於群體層面」。換句話說,這裡討論的偏好適用於一大群人的趨勢,但不一定適用於群體中的每一個人。以慣用手為例,從群體層面來看,一般人習慣使用右手,但有些人就是左撇子。我們知道90%的人都是右撇子,但這不表示左撇子有什麼問題,或者他們和右撇子大不相同。其他大腦偏側化(lateralization)的個體差異也是如此。對於90%的人來說,左腦主導語言,但這並不表示10%以右腦主導語言的人,在口說或書寫方面表現會比較差。
失衡行為的個體差異偶爾可能揭露了某些問題。例如,新手媽媽通常會朝左邊抱嬰兒,但患有憂鬱症的母親可能更常把嬰兒抱在右邊。如果你喜歡將孩子抱在右邊,是否表示你得了憂鬱症?絕對不是。然而,如果將喜歡朝右抱嬰兒的群體與朝左抱小孩的人相比,憂鬱症在前面那個群體中更為常見。本書探討群體層面和群體的趨勢,而非診斷或分析個人情況。
⋯⋯
當你閱讀本書時,有時會搞混左邊和右邊,但這不是你的錯。你沒有什麼問題。我有時會要你做一些奇特的腦力體操,我認為借助一、兩張圖片就可以克服左右混亂的難題。上頁圖2顯示了視覺系統的交叉作用,看起來很簡單:左側的空間進入右腦,反之亦然。右腦專門負責臉部辨識,導致我們自拍時習慣左臉對著鏡子。當我開始描述這種現象時,你必須想像一個人的臉位於視野中心,再想像兩個人面對面時,哪半張臉位於哪個空間,然後在你的腦海中再次顛倒左右,因為我們討論的場景是有人在照鏡子!
本書的編排方式是一次討論一種側偏好,這可能會給人一種印象,感覺側偏好通常是相互獨立的,但其實並非如此。例如,用手偏好(請參閱第一章)與我們對腳、耳朵和眼睛的側偏好(請參閱第二章)密切相關。擺姿勢偏好(請參閱第六章),也與我們在同一件藝術品中看到的光源方向偏好(請參閱第七章)有關。這並不表示某種偏好必然導致另一種偏好。我在不同章節討論不同的偏好,並不表示它們是離散和獨立的現象,許多偏好是相互關聯的。等我們單獨檢視過每項側偏好以後,我會在〈後記〉將這些偏好串聯起來。
第1章 慣用手:左撇子更優越嗎?(節錄)
最著名和最明顯的側效應就是慣用手。從群體層面來看,多數人偏好使用右手,從中便可輕易看出人腦是失衡的。慣用手並非新發現或新發展的側偏好,連《聖經》等古代文獻也曾提及。然而,不知何故,這種用手習慣卻成了被人研究最多但也最神祕的側偏好,人人都會注意到這種左右差異。專門探討慣用手的書籍有數十本,即便你沒有讀過其中一本,我猜你也曾想過自己為何會習慣使用某一隻手。一旦慣用手輕微受傷,我們便會深刻發現,另一隻手竟然如此無用,進而感到尷尬無比。
因此,本書最好先分析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左右手的習慣,但如此開篇也是最糟糕的。然而,我真的別無選擇。各位將在後續章節中發現,慣用手會影響(不是導致,而是影響)書中討論的其他多數側偏好。慣用手的影響錯綜複雜且無所不在,我研究別種側偏好時根本無法擺脫它。為了與其他章節的重點保持一致,我討論慣用手時會局限於日常生活,然後透過這個角度去描繪其他的側偏好。
右撇子占人口的比例有多少?我可以簡短回答,也能給出冗長的答案。簡短的答案是,大約90%的人習慣使用右手。那冗長的回答呢?右撇子占比多少,得看一個人的出生地,也取決於這個人的出生時間,還端賴他成長的文化和環境,以及他的性取向。這個比例甚至取決於一個人的(胚胎)發展軌跡,以及在出生過程中或者之前是否出了什麼差錯。這還取決於一個人的性別。話雖如此,取決的因素就只有這麼多。這些因素可能會將大約10%的比例推高一點,但也很有限。除了左撇子大會(儘管有左撇子的虛擬聚會,甚至還有一些面對面的集會,特別在8月13號的國際左撇子日﹝International Left Handers Day﹞),你永遠不會在某個時間、某個場所或某個文化中,找到一個超過50%的人偏好使用左手的龐大群體。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歷史。現代的圖像檔案中有大量關於慣用手的資料。我們可以查看一些圖片,譬如檢視重要文件的簽名照片,甚至查看數十年前的棒球卡背面,從中推斷某個去世已久之人的用手習慣。然而,這類紀錄只能追溯到這麼久以前。如果要問人類習慣用右手有多久了,該在哪裡找出答案呢?早期的文字紀錄非常罕見。例如,《舊約.士師記》第二十章第15–16節,描述了一場由700名左撇子或善用雙手者和26,000名右撇子戰鬥的場景。從這個比例(97%)來看,人類非常愛用右手。
然而,如果我們可以追溯到比《聖經》更久遠的時代,甚至回到數百萬年之前。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的狩獵方式顯示出慣用右手的跡象!舊石器時代的石器提供了有力證據,顯示當時的工具製造者是以右手旋轉石芯。從北京猿人製造的石器也能看到類似的模式。此外,幾乎每一種早期文化都會繪製人們從事狩獵之類的各種活動圖像。在某些圖像中(請參閱上圖3),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某個人只用一隻手投擲武器或手執物體。從克魯馬儂人(Cro-Magnon people)的手繪圖畫、對北美原住民藝術的考察,以及西元前2500年至1500年的埃及貝尼.哈桑(Beni Hasan)和希臘底比斯(Thebes)墳墓中,描繪人物用手從事技巧性活動的繪畫,便可看出人類對右手的強烈偏好。
有人調查過西元前15000年至西元1950年,繪製的一萬二千多件清楚描繪人類用單手做動作的藝術品,發現其中92.6%的作品都讓人物使用右手。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側偏好顯得非常穩定。舉例來說,在西元前3000年以前的圖像中,這個比例為90%;在西元500∼1700年的圖像中,這個比例則介於89∼94%。我們使用這種公認的不尋常研究技術,便可知道偏好使用右手的習慣,在過去五十個世紀裡基本上沒有改變!
然而,事情可沒那麼簡單。在出生於西元1900年左右的人之中,大約3%是左撇子,但在此之前和之後,左撇子的占比約為五十個世紀以來10%的平均水平。最棒的一組慣用手資料,基本上是偶然產生的。1986年,我那時還小,我的父母是《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的忠實訂閱者,就在那年9月,該雜誌最不尋常的一期版本寄到了我家信箱。它裡面有一張「刮一下、聞一下」(scratch-and-sniff)卡,超過1,100萬訂戶被要求辨識卡片上的氣味,回答一些人口統計的問題,然後將卡片寄回雜誌社。在人口統計的問題中,有兩題和慣用手有關,要求讀者填寫他們寫字和投擲時習慣使用哪隻手。調查結果令人難以置信。超過140萬人寄回填好的卡片,儘管慣用手似乎與嗅覺辨別(olfactory discrimination,這是最初啟發這項調查的問題之一)無關,但人口統計變量之間的相互關係足以透露某些訊息,尤其這組資料量十分龐大。
這批資料的原始報告指出了兩個關鍵情況。一個非常有趣,另一個則令人費解,還讓人有點擔憂。有趣的發現是,男性自稱是左撇子的可能性比女性高出約25%。第二項發現引起了多數人關注。在1950年後出生的受訪者中,左撇子相對普遍(請記住,這項調查是在1986年做的,因此1950年之後出生的人當時只有36歲以下)。但在出生較早的老年人之中,左撇子則愈來愈少,人數直線下降,在出生於1920 年或之前的受訪者之中,只有3%或4%是左撇子。第二組涵蓋同一時期的資料規模比較小(這次的抽樣對象是英國公民,不是美國公民),也透露出相同模式。1800年代末至1920年間出生的左撇子跑去哪裡了?在這個群體中,左撇子比率是否真的如此低,或者更糟的是,左撇子的死亡率是否比較高,因此年老的左撇子占比才這麼低?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