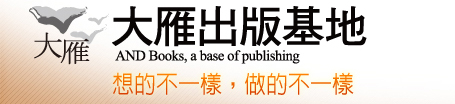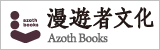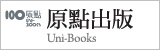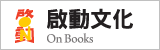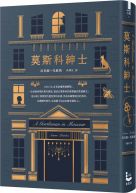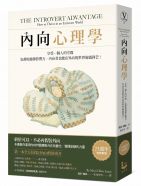當你渴望知道自己是誰,就是上路的第一步。
西方最重要的新時代靈修最新經典著作!
101歲覺悟者跟隨大師腳步的珍貴記錄,
101歲覺悟者跟隨大師腳步的珍貴記錄,
九型人格鼻祖葛吉夫的第四道體系全揭秘,
每一頁都閃耀著智慧!
王季慶、張德芬二大名師共同推薦。
【大師推薦】
葛吉夫是一位開路先鋒,開啓了一個對靈性生活的全新觀念。他受到很大誤解。因為他對傳授知識沒興趣,他不想給你慰籍;也沒興趣給你美麗的理論、洞見、幻像;他對你的眼淚、情感、情緒,都沒興趣;他不想讓你崇拜他,他只想要蛻變你。——奧修(Osho)
我們必須在自己內在和周遭,創造出一種層次的能量,一種能夠抵禦周遭影響,又不會自行衰退的專注。它必須接收一股更為主動的力量,讓它不僅能抵禦,更能採取行動,在不同層次的兩種能量流之間,找到一個穩定的位置。維繫這種平衡的狀態,是我們在意識工作中一直會遇的挑戰,也是我們意識工作每一刻都要面對的困難。——珍妮·迪·薩爾斯曼(Jeanne de Salzmann)
一向非常喜歡葛吉夫的教導,可惜有關著作都比較艱澀難懂。這本《生命的真相》用簡單易懂、通俗的語言闡述葛吉夫的教誨,讀來令人欣喜。發展覺知和覺察能力是靈性成長最重要的修持,本書有極為明確的闡釋,為在靈修路上摸索前進的我們提供了一盞明燈。——身心靈作家 張德芬
【誰是葛吉夫?】
他是諸多西方藝術家服膺的靈修教父!美國建築大師萊特Frank Lloyd Wright 、爵士樂史上最偉大即興演奏家Keith Jarrett、《歡樂版人間》經典Mary Poppins角色創造者P.L.Travers……皆受葛吉夫影響極深。
奧修曾說,「只有少數勇敢的人,才能進入葛吉夫這樣一個人的世界。他需要極大勇氣,要有赴死的勇氣,因為唯有如此才有重生。他不是個教父,他是師父。」
葛吉夫於1866年生於俄羅斯和土耳其交界的高加索地區,他從童年起就渴望瞭解人類存在的奧秘,並且深入研究宗教和科學來尋找答案。他發現這兩種體系從它們自身看來都是令人信服和前後一致的,但如果將它們所依據的前提作出改變的話,就會得出矛盾的結論。於是他相信無論是宗教還是科學都無法單獨解釋人類生死的意義。同時,葛吉夫堅信古代曾經存在著一種真正且完整的知識,並以口頭的方式被一代接一代傳承下來。
他花了大約二十年時間尋找這些知識,最終,葛吉夫發現了一些被遺忘的素質層面的知識,它融合了各種偉大的傳統信仰。葛吉夫把它稱為「古老的科學」,但卻沒有明確告訴我們它的來源,以及它的發現者和保存者是誰。這種科學像現代物理學一樣看待這個可見物質組成的世界,認可質能相當性、對時間的主觀錯覺和廣義相對論。但是這門科學的探索並未就此停止,只是將受控的實驗中能夠衡量和證明的現象作為唯一的真相來接受,它還會去探索感官感知範圍之外的神秘世界,探索對另一種實相的覺察,以及超越時空的無限狀態。其目的就是為了理解人類在宇宙秩序中的地位,以及地球上人類生命的意義,同時讓我們內在真正瞭解和體驗兩個世界的實相。這就是關於素質層面的科學。
【何謂第四道?】
葛吉夫的教學有古老的淵源,以祕傳基督教的方式呈現,他有二十世紀的達摩之稱,奧修更讚譽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老師。葛吉夫所創立的「第四道」修行體系是一門整合身體、感受和思維的修行法門,他將傳統的修行方式歸納為三條「道路」,包括:著重於駕馭身體的「苦行僧之道」、基於信仰和宗教情感的「僧侶之道」,以及專注於發展頭腦的「瑜伽士之道」。第四道,則同時對這三個部分下工夫,讓人的身體、理智與情感同時運作,維持平衡,方法是嶄新的,是適合每個現代人修道的新工具。
※這是一部你可以收藏和參照一生的經典著作。
《生命的真相》是一本101歲覺悟者對「第四道」的修行筆記。作者薩爾斯曼夫人,是二十世紀靈性大師葛吉夫最親近的弟子,她在30歲遇見這位偉大導師,71年來透過「律動」(movement)的方式,活出葛吉夫的教導,本書是後人整理她生前筆記,提供了關於葛吉夫靈性教學的全新洞見。從「對意識的召喚」、「向臨在敞開」、「我是誰?」⋯⋯共12大章140節,近20萬字,每一字一句都是對生命的深刻提問,凝鍊出「第四道」之於她的精神頓悟與體驗。
無論你在靈性之路上,跨出了多遠,本書都會是一面鏡子,可以照見你已經領悟了什麼;但更重要的是,它將照見你未曾領悟的東西,而這些正好能為你指出前進的方向。
※第四道工作,帶領我們從「清醒的沉睡」狀態解放出來!
葛吉夫的教學有古老的淵源,以祕傳基督教的方式呈現,或「素質層面知識」的教導。「第四道」是葛吉夫設計的一門整合身體、感受和思維的修行法門。葛吉夫將傳統的修行方式歸納為三條「道路」:著重於駕馭身體的「苦行僧之道」、基於信仰和宗教情感的「僧侶之道」,以及專注於發展頭腦的「瑜珈士之道」。第四道並不是透過紀律、信仰和靜心的路徑,而是喚醒另一種智慧——瞭解和理解,就能讓我們從「清醒的沉睡」狀態解放出來。
透過有意識的努力達成有品質的思維和感受,從而具有一種能夠清晰覺察與愛的全新能力,本書對葛吉夫的理念和方法提供了完整而獨特的指導。
※生命的律動,在另一個空間、另一個世界的體驗中獲得重生。
《生命的真相》是一本生命指南,這本靈修筆記的每一頁都閃耀著智慧,讀起來就如同親自跟隨葛吉夫的足跡,每一步都有新發現。
《生命的真相》是一本生命指南,這本靈修筆記的每一頁都閃耀著智慧,讀起來就如同親自跟隨葛吉夫的足跡,每一步都有新發現。
除了帶領我們覺察自己,尋找如是存在的生命真相,引領我們在另一個空間中重拾心靈的自由,活出完整的「臨在」。本書亦解剖葛吉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的「神聖舞蹈」教學,透過這樣的生命律動,讓我們瞭解大多時候,我們就像一部自動運轉的機器,不帶覺察,唯有透過「瞭解自己」,也就是當下每一刻的意識提升,才能讓內在真正的自己甦醒過來!
【本書特色】
◎ 西方最重要的新時代靈修體系最新經典著作,九型人格鼻祖葛吉夫的第四道體系全揭秘!
◎ 一位101歲覺悟者的71年修道證道,本書是作者薩爾斯曼夫人畢生跟隨葛吉夫學習的珍貴筆記。
◎ 全文洋洋灑灑近20萬字,12大章140節,收錄最完整、最精華、最透徹的葛吉夫第四道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