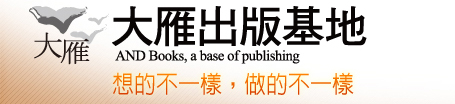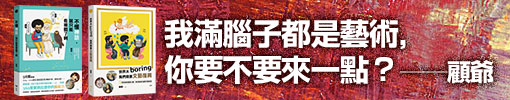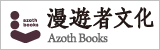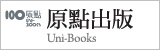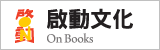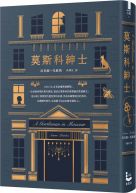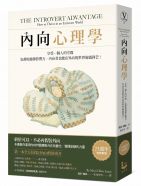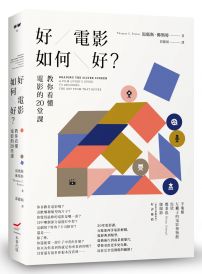前言 看完電影之後
好!有兩個人走出電影院。我知道,這聽起來像爛笑話的開場,不過,請跟我一起動動腦筋吧!他們叫蕾西與戴維,在隨手把爆米花桶與汽水罐丟入垃圾桶後,便走上天色漸暗的街道漫步閒聊。
蕾西說:「整體來說,這部電影還滿忠於原著的。你覺得呢?」
「棒!」戴維說:「這就是《瘋狂麥斯:憤怒道》(Mad Max)。場面龐大、吵鬧、瘋狂,是我喜歡的那種電影。妳覺得呢?」
「我也覺得很棒。但不是故事棒,而是電影幕後的設計構想,讓它像是藝術品。」蕾西想了一下,「算是一部瘋狂吵鬧的藝術創作。」
「藝術?我不認為那算是藝術。藝術屬於那些外國人,像是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費德里柯.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還有那個日本人叫什麼來著?或是伍迪.艾倫。妳懂我的意思吧?就是那種煩悶的東西。」戴維說。
「那你是說動作片不是藝術囉?」蕾西說。
「我的意思是,誰管它是不是藝術呀!只要有好的故事加上很多打鬥場面就可以了。有飛車衝撞、爆炸、辣妹、噴火的吉他。否則還有什麼呢?」戴維有了點興致。
「就是怎麼呈現出這樣的畫面──怎麼呈現動作、拍攝一個畫面時把攝影機擺在哪裡。讓電影看起來是最後呈現的樣子。當然,還有音樂……」蕾西說,她試著不顯露出優越感。「所有的其他東西,你想想看。」
「我看妳是故意捏造所有的其他東西吧!妳說說看,像是什麼?」
「就拿主要的反派角色來說。他是不是叫『不死老喬』?他的樣子很像黑武士。要知道,光是怎麼幫他戴上面罩和呼吸器,就夠瞧的了。不過,我覺得他看起來比較像賈霸。」蕾西說。
「說到這個,我看另一個同黨更像賈霸,就是那個腳丫大得像花盆,有個銀鼻子的食人獸。他的樣子有夠噁心的。」戴維說。
「除了角色之外,這部電影也是視覺的曠世鉅作。誰會想出那些拿著桿子在車輛之間撐桿跳的瘋子?還有取鏡的技巧。整部電影,每一個場景及鏡頭畫面,看起來都十全十美。我不知道要怎麼解釋才夠清楚。藝術,你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蕾西說。
「隨妳怎麼說吧。」戴維說:「妳想太多了,教授。我只要看電影就好了。」
歡迎加入隨興電影評論國,讓我們想一想他們剛才聊過的內容。他們其實都對:戴維表現出「愛怎麼看電影,就怎麼看」的立場,把看電影當成純粹的娛樂。可是,蕾西總覺得自己還有更多看法沒說出來,即使她不完全清楚那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裡有個問題要問:什麼是「所有的其他東西」?這又帶出另一個問題:這些東西重要嗎?第三個問題:我們應該在乎嗎?若應該的話,又是為什麼?
以上三個問題值得解答,所以我在此稍微重組一下。第一,不管是由什麼組成的「所有的其他東西」,絕對重要。
即使簡單得像是重新安排一個房間的家具那樣,上演的劇情也會改變,因為劇中角色無法像第一次那樣,循著原本的走位在不同的空間裡演戲。若不改走位,原本要拍攝的正面鏡頭,可能變成拍到了後腦勺。當然,如果那是你要的畫面,那很好。不過,那是一個場景中的一個選擇。
在《瘋狂麥斯:憤怒道》裡,有許多飛車追逐片段構成了整部電影的絕大部分。其中一段情節是,英雄們必須穿越一個狹道,那是幾噸重的岩石被炸開後再清理過的洞口,是陡峭峽谷裡的一個石圈。這座峽谷被一群瘋狂的機車黨占領,他們專門勒索過路費,就像約翰.韋恩拍的大部分西部片裡的阿帕契族印地安人那樣,在裸岩上站崗,探查地盤。
芙利歐莎(莎莉.賽隆飾演)本來已經跟機車黨交涉好,但對方卻反悔了;機車騎士轟炸部分峽谷,來抵禦芙利歐莎的敵人(也是她最近的主子)「不死老喬」的攻擊時,她帶著車上的眾人逃亡。
所以,在這個橋段裡有一些選擇:有多少名騎士跟芙利歐莎談判?其他餘黨在峽谷的哪裡?什麼原因驅使他們在沙漠裡穿得像毛球一樣?在岩石坍方之前與之後的峽谷路況?
在談判過程中,其他人在哪裡?每個鏡頭都牽涉到一百個決定……
在拍攝一個鏡頭時,要考慮的項目有:人物(地點、人數、攝影機的距離)、取景、攝影機的角度與距離、燈光、道具、拍攝持續時間、音響清晰度、背景音樂、哪個畫面先拍、哪個後拍。換句話說,有多少人在場,他們穿什麼(或不穿什麼);要集體入鏡或拍攝單人鏡頭?要近距離拍攝或在指定時間內推近拍攝?其他還有:要用什麼背景音樂來襯托動作?燈光要多亮?說話要清楚或含糊?也就是說,要用到多少視聽元素才能表達這個場景?
至於第二點,我們應該在乎嗎?那倒未必。一如戴維的觀影樂趣告訴我們,他很滿意自己看到的,他不需要了解更多。總之,電影院不是電影學校,我們去看電影也不會被打分數。然而,蕾西注意到那部電影裡獨特的一面:有人把這部電影裡該有的視覺、聽覺、感覺的訴求,都製作到位。無論他們做得好不好,整部片是經過許多選擇,與處理一大串事件和變化,才能完成的。
有沒有興趣了解電影是如何整合的,純屬個人選擇。針對某些電影,如果不去追究,也許會改善觀影的感受。還有,電影會使我們處於被動狀態:坐在電影院裡,出現在銀幕上的腦袋可以有十呎那麼巨大,因而把我們制伏了。觀看大銀幕而不去解析,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時下的電影都塞滿了動作變化且劇情貧瘠,不去質疑這些熱門鉅片,的確比較容易,也相當自然。
……
在討論之前,有個大問題:「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些?」單純是為了「樂趣」。當然,你可以將這門學問運用在課堂上或部落格裡,成為知名的評論者。你甚至可以神氣地向朋友炫耀這種分析能力。不過,我不建議你這麼做。當然,應用分析策略是很棒的腦力激盪,我們都需要多做一些,但重點不在於此。學習分析電影的最大說服力,是你將會享受到更多樂趣。能夠侃侃而談《星際大戰》(Star Wars)或《哈比人》(The Hobbit)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不覺得很酷嗎?或者我們能針對劇情範圍以外的東西聊得更深入?那種樂趣則是來自多方面的。以下是一些可能吸引你的樂趣。
樂趣一
如果蕾西繼續探究,比起戴維,她將會從未來的觀影經驗中享受到更多樂趣,而戴維的觀影樂趣往往是影片表面的劇情—誰說了什麼、發生什麼事、哪裡有趣、哪裡讓人難過等等。這樣並沒有錯,但還有更多好玩的事物等著你去挖掘。學習如何看出更多,並不會沖淡觀影的樂趣。這是容易讓人誤解的文化現象—如果我們分析正在閱讀或欣賞或聆聽的創作,會抹煞我們「單純」的樂趣。這是真的嗎?
那麼,為什麼那些音樂達人要把平克.佛洛伊德(Pink Floyd)、圖派克(Tupac)、披頭四(Beatles)、珍珠果醬(Pearl Jam)或什麼人唱的歌詞,挖掘到最後一絲的含義呢?
你真的以為,他們那樣追根究柢就會失去原先的快感嗎?其實,沒有人比文學教授更能享受閱讀文學的樂趣。當他們同時在考慮五、六個,甚至十多個不同的解釋、指引和意義時,就像一台齒輪不停轉動的機器。他們根本不會覺得掃興,反而可能擁有兩到三倍的樂趣。
樂趣二
從爛片中也可以找到樂趣。爛電影,就跟好電影一樣,也需要運用到許多相同的技術。我們將拿出一些例子來說明。不只如此,當你變成更有成就的評論者時,就可以看出一些電影出錯的地方,從而獲得樂趣。反觀另一面,你也能開始看出好電影所具備的條件,而這些對於經驗不足的觀影者來說,很容易忽略。
樂趣三
懂得多一些,是難倒朋友的好方法,誰不喜歡呢?瞧一瞧剛才提到的戴維,他正在思索自己到底錯過了電影裡的哪些東西。他當然不服氣,因為蕾西的鑑賞並不是那麼有說服力,可是,他發現蕾西看那部電影看得那麼過癮,導致他開始思索,並打算下次看電影時,要用不同的角度來看看電影裡有沒有藝術這門學問。如果稍微專心一點,注意一下劇情的幕後作業,可能會看見一些東西,就像蕾西那樣。
你是戴維還是蕾西?你是那位開心觀影、不去思考的人,純粹把電影當成消耗品,看過就忘?還是希望從觀影經驗中獲得多一點東西,並跟朋友聊聊這個有趣的話題?當你看出片中的某些東西,卻又不知其所以然時,不會想要多加了解嗎?最重要的是,你想不想把看電影當成是個人的真正經驗?那麼,何不一起踏上這段旅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