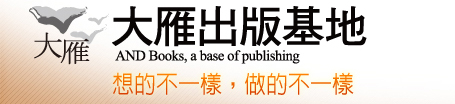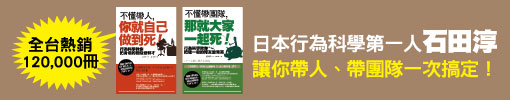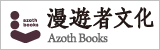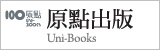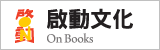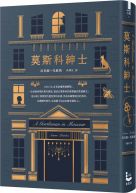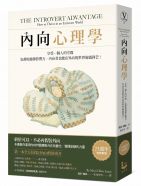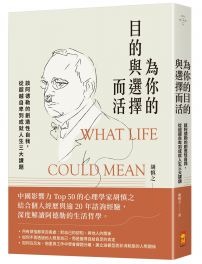我們的行為和情緒,都隱含著目的
我一直認為,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是一種心理哲學,他創造了很多讓我們精神為之一振的理論,他的許多觀點都極具哲學智慧。因此,我願意稱之為有力量的心理學,同時也有理由相信,這是一種可以讓我們內心強大的心理學。
阿德勒是心理學界的三大巨頭之一,曾擔任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主席,後來因為與佛洛伊德的心理學觀點不同而離開了精神分析學派。很多人非常困惑,為什麼阿德勒心理學和佛洛伊德心理學有那麼大的出入,甚至有些學者認為他們的觀點是對立的。原因在於,阿德勒是精神分析學派內部第一個反對佛洛伊德心理學體系的人。阿德勒後來創立的個體心理學,與佛洛伊德的學說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見解。阿德勒反對佛洛伊德以本我為中心的泛性論(即把人類的所有行為都視為由性本能所驅使的心理學學說),更強調自我的功能,以及人格發展中的社會因素。佛洛伊德認為人格動力是欲力(Libido)──一個和性本能相關的動力指標,而阿德勒則認為人格動力源於人的自卑感。很顯然,這是兩種相對立的人格理論。
對於「自卑感」的來源,阿德勒最早從生理學角度對此進行闡述,即生理上的缺陷引發了自卑感,後來又將原因有意識地轉向主觀的自卑感,認為自卑感起源於個體生活中所有不完滿或者不理想的感覺,不管這種感覺是基於客觀現實,還是屬於個體的想像。在《阿德勒談人性》(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等著作中,阿德勒還將自卑感的來源推得更加遙遠,認為自卑感來源於人類祖先。
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受阿圖爾.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一七八八至一八六○年)的「生活意志論」,以及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一八四四至一九○○年)的「權力意志論」的影響很深,主要體現在阿德勒理論中的「目的論」,或者稱之為「動機論」,即我們為了什麼而行動。
阿德勒的目的論告訴我們,人都是為了某種目的而活著,都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採取相應的行動。因此,無論你過去經歷了什麼,都將對你如何度過今後的人生沒有影響。
在這裡,我們能看到阿德勒與佛洛伊德之間的一個很大分歧,即佛洛伊德的理論強調過去的經歷會影響甚至決定個體的行為,認為人現在的不幸是由過去受到的傷害或者心理創傷所造成,我們稱之為「原因論」。但是阿德勒的「目的論」對此進行了否定,認為決定我們自身的不是過去的經歷,而是我們賦予經歷的意義。
可能會有很多人認為這是兩個完全對立的觀點,但我傾向於它們不是對立關係,而是進化關係。阿德勒並不是完全忽視過去經歷的作用,而是更多地強調如何利用被給予的東西,以及賦予過去經歷什麼樣的價值,這才是現在的我們所面臨和需要考慮的,主導權在我們手中。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而是沉浸在過去的束縛中,那麼我們將無法突破和改變現狀。
恐婚是現在的年輕群體中一種比較常見的現象,甚至有些人在面對被催婚或者逼婚時,會非常憤怒。為什麼有的年輕人那麼恐婚?如果從佛洛伊德的「原因論」來解釋,一個人之所以會對婚姻充滿恐懼和不信任,往往是因為小時候經歷了父母的離異,或者被身邊一些不好的婚姻狀態所影響。但是,並不是所有離異家庭的孩子都會對婚姻充滿恐懼和不信任。因此,阿德勒的目的論認為,不想進入婚姻是這個人的「目的」,為了說服自己達到這個目的,於是搬出了小時候的痛苦經歷作為解釋。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恐婚也是因為不結婚有利己的部分,比如可能是我們更喜歡目前單身生活的現狀,因為這種現狀讓自己更加安心和自在。
在家庭動力學裡,我們經常會遇到這樣一種情況,就是很多人不能好好地進入一段親密關係,比如不能結婚。不能結婚聽上去是因為自己的某些原因,或者曾經受過某種傷害,但是不能結婚還有一個原因──無法離開他原來的家庭,因為在那個家庭裡有一個需要照顧的人,並且自己可以從照顧那個人的過程中獲得優越感。就好像有的姊姊會犧牲自己去照顧弟弟,她無法離開她的原生家庭,因為她的目的是想要打敗自己的弟弟,成為一個對於家庭來說有更大貢獻的人,從而被更多人看見。
小A今年三十三歲,有一個交往了五年的男朋友,但是他們一直無法順利地進入婚姻關係。原因是小A總是一邊抱怨家人對她索取太多,一邊又幫弟弟還賭債,即使自己已經很累了,也一樣會竭盡全力地幫弟弟收拾各種「爛攤子」,並且還因此辭掉自己的工作。為此男朋友和她爭論過很多次,但是小A並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甚至覺得男朋友太不近人情了,一點都不為她著想,最後直接跟男朋友提出分手。表面上小A是因為男朋友的不理解而提出分手,實際上是她故意為之。她的目的絕不是進入一段婚姻關係,而是更想要成為一個對原生家庭提供更多價值的人。
和小A一樣,很多時候,我們總會為自己做的事情找個看似合理的理由,於是就有了「原因論」,常見句型為「我就是因為你,所以才會變成這樣」。從精神動力學的角度來講,這是一種自我防禦機制,我們稱之為「合理化」。這是很多人無法意識或者無法承認的一點。
在導言裡,我曾經提過這樣一句話:「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假使我們從佛洛伊德的原因論來看,這句話會讓我們更多地感到悲觀或者消極,因為只要有一個不幸的童年,似乎我就要用我的一生去治癒它。但是如果從阿德勒的目的論來理解的話,會讓我們感覺到更有力量,那就是你可以做一個選擇,到底是要去療癒你的童年,還是為你不幸的童年重新賦予一個意義,然後成為一個幸運的人。
在我的工作中,當來訪者總是對父母給她造成的傷害而耿耿於懷時,我會問她:「你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改變你的父母嗎?」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是想要表達對現實狀況的不滿,想要有人來為自己的生活負責。
曾經我也抱怨我的父母,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我的父母會這樣對待我,特別是我父親對我的那種嚴厲教育。後來,透過學習心理學,特別是學習了阿德勒理論,我開始嘗試重新定義我對父母的抱怨。我的目的是為了不要成為他們,並且想要和我的孩子相處得更加舒服自在。因此,當我重新為這件事情賦予一個新的意義以後,反而父母對待我的方式就變成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正是因為經歷了那些,所以我對自己的孩子,包括對親子關係和家庭教育都有了不一樣的理解。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反而挺感謝我的父母,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自己和父母的關係。所以,我成為了一個幸運的人。
總的來說,原因論更多是為了歸因,從而把一件事情合理化,而目的論是為了重新給這件事情賦予一個新的意義或者目標。事實上,我們應該擁有怎樣的人生,全由我們如何詮釋所決定。
自主選擇是一種能力
我一直認為,阿德勒的心理學對於家庭教育是非常有效的,並且能夠給予很多困惑的父母一些指導,理清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關係,理解在家庭成員互動的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進行家庭教育時,有多少人知道家庭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有很多人會以培養一個聽話懂事的孩子,作為我們的教育目的,但是真正的家庭教育的概念是,如何讓孩子知道自己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並且自主地設定人生目標,以及在完成這個人生目標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屬於自己的生活風格。
每個孩子在很小的時候,都有自己的一個人生目標,比如我們會說:「我要當一個工程師,我要當一個科學家,我要去遨遊太空……」但是在家庭教育的過程中,很多父母並沒有真正地讓孩子去確認這個目標,甚至教育孩子的方式跟孩子的目標是有衝突的。父母既想讓孩子有創新意識,敢於冒險,又不希望孩子太有主見,甚至不允許孩子有任何錯誤,一旦犯錯必然受到懲罰。這顯然跟孩子實現人生目標的方向是相反的。一旦雙方的目標不一致,那麼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權力鬥爭就會發生。權力鬥爭,本質上就是孩子說「你看看我」,而父母說「你聽我的」。比如一個孩子在吃完飯後很想看電視,但是媽媽讓他去寫作業。那孩子說:「我看完電視再寫作業,作業我一定會完成的。」這一刻,媽媽就有挫敗感了:「不行,你要聽我的,現在必須去寫作業。」其實兩種方式對結果都沒有太大影響,但是對媽媽的優越感是有影響的,因為孩子不聽她的話會讓她感覺到很挫敗。
我的兒子在六歲左右時,有一天他跟我說,他想當一名火車司機。當時我和孩子討論,他為什麼想當火車司機。首先,我需要知道他的動機。孩子跟我說,火車司機很酷,還會鳴笛,而且開火車可以去很多地方,看不一樣的風景。聽到這裡,我要跟他討論的是,為了成為一名火車司機,他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準備,比如火車司機要接受什麼樣的訓練,要考取什麼樣的證照,要形成什麼樣的生活習慣,然後才有可能達到成為火車司機這個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會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他,老爸想成為一位非常專業的心理諮詢師,所以我會為此學習很多相關知識,完成必要的心理學培訓課程,最後才能成為一名專業的心理諮詢師。
當我這樣跟他討論的時候,他能看到我是如何為了自己的目標而努力,那麼慢慢地,孩子就會知道,如果要達成某個目標,他需要經歷和完成哪些事情,並且做出哪些選擇,比如當他需要在「完成學業」和「玩耍」之間選擇的話,出於本性,他肯定更想去玩,但是為了達成設定的目標,他可能會選擇學習。當我們發現自己有選擇的權利時,人生就會充滿積極和進取,我們更願意去實現和創造一些東西,從實現和創造的過程中獲得一種優越的感覺,而不是透過幻想或者想像獲得優越感。
然而,有些人是生活在過去的,對於當下完全沒有人生目標。我們經常說「好漢不提當年勇」,當一個人總是提起「當年勇」,那就說明了他缺乏對未來的生活目標,或者說現在的生活並沒有讓他感覺到有任何的優越感,而恰恰「當年勇」可以提供他一種優越的體驗。當然,對過去念念不忘的人,不僅僅是因為對未來沒有太大的目標感,也可能是我們沒有了追求目標的動力,或者說是失去了實現這個目標的勇氣。
比如,一些無法從失戀中走出來的人,他的目的就是選擇讓自己待在失戀的痛苦裡,不去進行下一段戀愛。這樣他會覺得自己是一個痴情的人,是一個受到傷害的人,這是他的優越感。他不需要再去冒險談一場困難的戀愛,目前的狀態就變成了他的舒適圈。在這種情形下,阿德勒的目的論就能夠很好地幫助他去選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每個人的選擇都是不一樣的。有些人遇到事情就會去解決,但有些人一旦遇到事情,他就會停留在情緒中,比如魯迅筆下的祥林嫂,祥林嫂之所以沒辦法從她的悲傷中走出來,是因為她渴望得到別人的同情。於是,為了得到同情,她一次又一次地訴說著自己的悲慘故事。當然,這是她的選擇,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的,這種選擇缺乏一種勇氣,那就是讓自己從糟糕的情緒狀態中走出來的勇氣。
情緒,有的時候也是一種選擇。阿德勒提過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在一位母親正因為自己孩子的作業沒有寫好而發火時,家裡的電話鈴響了,打電話過來的是學校的校長,那位媽媽的態度一下子就變得很平和,根本不會讓人感覺到一秒鐘之前她還在憤怒之中。這是因為兩種情境中的目的是不一樣的,媽媽情緒恢復平和的目的,是為了能與校長好好地交流,而對孩子發火的目的,是為了發火,而不是為了讓孩子改變。因為有時候,我們對孩子發火不是為了教育,只是為了洩憤。
當我們發現情緒是可以選擇的,那麼,我們就能意識到,情緒背後往往也包含著某種目的,無論是意識層面的,還是無意識層面的。比如,在有些情況下,憂鬱的狀態也暗含著我們無意識層面的目的和需求。從目的論出發,當我們意識到自己能夠選擇的時候,我們便可以選擇過去的經歷對自己的影響。關鍵在於,你想要達成的目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