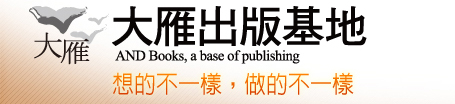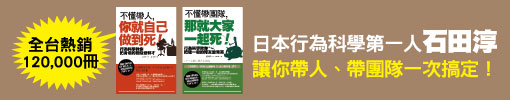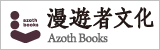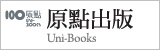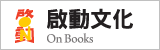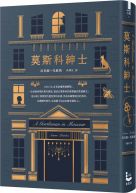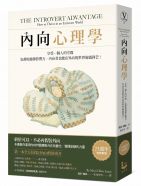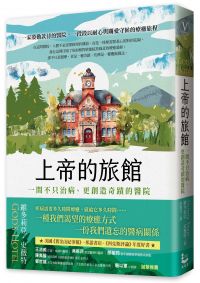【前言】
我第一次做大體剖檢,是在病理學院臨床見習的第一天。
我進醫學院頭幾個月當然就看過也接觸過屍體,不過那些遺體都經過處理,血管裡似乎不再有福馬林的氣味。我的手和手指因觸碰他們而起皺,但除了氣味,他們看起來幾乎就像塑膠假人。
然而,那回掀開眼前那具遺體臉上的覆蓋物時,我嚇了一跳。是貝克先生,是我行醫後實際接觸的第一批病患!貝克先生體型矮壯,是個老菸槍,也是所謂的「藍色膨脹者」。肺氣腫毀了他的肺,讓他的胸部腫脹如桶。他的脖子粗短,嗓音粗啞,動脈和靜脈都很難抽血,但他對我們始終非常體諒,個性開朗又有活力。我確信他應該會治療順利,出院返家。顯然事情並不如我的預期。
貝克先生消失了
當我觀察他的遺體時,心中開始出現疑惑。我知道那是貝克先生,但看起來真的不像他。或者可以這麼說,那遺體只是很像貝克先生,就像蠟像館裡的克拉克.蓋博或邱吉爾一樣,看起來像他們,但其實不是。
我看著病理學家拿起電鋸,動手剖開貝克先生的胸腔壁,取下濕潤、呈蜂窩狀的肺部,將兩邊的肺臟分開秤重,先右肺,再左肺。接著他取出大而沉甸甸的心臟,心臟右側因肺病而肥大。他記下心臟的公克數。接著他剖開腹部,同樣取出肝臟、脾臟、胰臟和腎臟,分別秤重,再記下公克數。他逐一檢查大大小小的血管,並記下注解。隨後,電鋸移向頭部。裡面自然是大腦,看起來就像教科書裡的照片一樣,呈灰色海綿狀,質地類似鵝肝醬,單調而無趣。這時,貝克先生的解剖告一段落了。我們完成了。一切結束。就這樣。他的體內沒有其他東西了。
我察覺自己心中浮現一股異常的失落。竟然看不到其他東西了。在那些彎彎曲曲的腸子之間,沒有任何隱晦,沒有任何未經探索或無法探索、如小小黑盒子般無法打開的某種東西隱藏著。是的,貝克先生徹底消失了。經過剖檢之後,他的身體就像一套棄置在角落的衣服。
有什麼東西消失了。究竟是什麼?是貝克先生的呼吸?他的動作?還是他的體溫?後來我才明白,當時我想找的是某樣東西,某個無法打開的核,就像剖開棒球後在球中央發現的東西。我想找的是難以抹滅的貝克先生,是病理學家的電鋸無法打開和破壞的東西。然而,那裡頭沒有那樣的東西。我親眼見證了。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那樣東西過去在醫學裡有個名稱;它存在於有生命的人體內,但人死後就消失了。事實上,它的名稱有兩個。第一個是spiritus,英文裡的spirit(精神、靈魂、心靈)就源自於它,只不過拉丁文的spiritus不像英文的spirit那麼虛無。spiritus就是氣息,是生命體具節奏感的規律呼吸,是屍體明顯缺乏的東西。spiritus是人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後散逸的東西。
另一個名稱是anima,通常譯為英文的soul(靈魂),但拉丁文較能表達貝克先生與他的遺體之間的第二種明顯區隔—無法動作。因為anima其實不是抽象的「靈魂」。anima是驅動身體的無形力量,它不僅讓身體有意識地動作,也讓身體在無意識之間動作,生命體時時刻刻出現的小動作都是由它驅動的,如手指的微微震顫、每秒撼動軀體一次的心臟搏動、胸腔微微的起伏等。這些動作讓我們感覺到某人活著。古代醫學留意到,在遺體中,anima和spiritus一樣消失無蹤。
儘管如此,我投入醫界時,spiritus 和anima 等字詞都已經從醫學用詞裡淘汰了。當時的我找不到合適的概念來描述我見到的情景。或許「剖檢」(autopsy,來自希臘文的auto-opsia,指親自觀看)這個詞的出現,讓那些字詞從西方語彙中消失了。也或許就是那個小小的黑盒子消失了。
我參與貝克先生的大體剖檢時,事前完全沒想過他的spiritus 或anima 消失了。我甚至不知道那樣的概念曾經存在。不過,我的確把他的遺體的影像封存在腦海深處,就像一套皺巴巴、遺忘在白色無菌室角落的衣服。
西方解釋身體的第一套理論
家人得知我決定就讀醫學院時都很震驚。我的家人當中沒有人是醫生,追溯整個家族歷史,也沒有人當過醫生。醫學工作對我們這樣的商人或知識份子家庭來說是勞力的工作,對我來說也太辛苦。不過有機會接觸天主教所謂的「末事」─—死亡、復活、天堂、地獄、煉獄,讓我對醫學深感好奇。此外,我也喜歡醫學要求公平對待每個人的概念。於是我向家人保證,我會從毫不耗費體力的科系踏入醫學界—精神醫學。榮格的研究令我著迷,我希望自己也能過他那樣的生活:上午在蘇黎世湖畔的石砌屋裡為高收入的優秀患者看診,下午寫作和授課。
醫學院頭兩年的授課內容是基礎醫學,如解剖學、生理學、生物化學、藥理學。接下來的兩年是臨床教學,學生得以將所學應用在真正的病患身上。我沒料到自己會喜歡這個部分,但我確實喜歡,那其中有許多部分與心理學有關。我發現自己喜歡探究「病史」─—病患訴說的故事,因為當中隱含了患者症狀的真實意義。我喜歡為病患檢查身體,因為真正的病因就寫在他們的身上,只不過我必須能解讀出來。我也喜歡分析事實,得出結論,也就是診斷、治療和處方。
醫學院畢業後,我開始接受精神醫學的訓練。不過我很快就發現,精神醫學從榮格之後已經有所不同了。如今我們認為精神異常起因是大腦,是化學物質失衡的結果,治療不是靠分析,而是藥物,通常效果很好。因此我沒成為精神醫學家,而是到縣立診所看診,之後轉往鄉間執業。後來我又回頭接受更多訓練,完成三年的住院實習,到社區診所工作,然後升為醫療主任。
那幾年當中,現代醫學—─包括其邏輯、診斷與治療方式等—─的威力讓我愈來愈佩服。然而,偶爾我還是會遇到類似貝克先生的情況,並陷入思索。出生的那一刻,死亡的那一刻,還有知道病患即將生病的玄妙時刻。這些一再證明某個難以捉摸卻又共同擁有的世界確實存在,生命在其中出現與消逝;這些也證明了有形效應的無形連結。
我很自然的以為現代醫學已探索過那種現象,因而開始研究現代醫學的探索成果。很快我就發現它們的名稱都非常無聊:「醫病關係」、「安慰劑效應」、「心身症」、「祈禱效應」。此外,它們也被歸入心理學領域,以心理分析來處理,也就是和我看到與感覺到的身體是區隔開來的。
後來,我轉向替代醫療尋找答案。中醫和印度醫學確實為我提供一些見解,因為他們以流動或堵塞的、平衡或失衡的來描述身體,這樣的觀點或許能解釋我從病患身上感受到的無窮能量。然而,中醫和印度醫學的語言及文化與西方醫學截然不同,我很難將他們的觀點和我自己的整合在一起。
就在我為此感到沮喪時,偶然發現的一本書為我帶來了驚喜。那是中世紀某位德國修女的行醫紀錄,譯自拉丁文。我從書中簡介得知,賓根的希德格(Hildegard of Bingen,譯按:又譯做聖賀德佳)是十二世紀德國神祕主義者及神學家,更讓人驚訝的是她也是執業醫師,還撰寫了一本關於她的醫學概念的著作。《希德格的醫學》(Hildegard of Bingen’s Medicine)不是了不起的名著2,卻令人振奮,因為屬於那套醫學概念的世界,不但與我多年前觀察到且封存在腦海深處的現象相符,西方世界也曾經知曉並加以運用過。於是我開始研讀希德格的醫學。我開始明白,我們的醫學—亦即現代醫學—不是西方用來解釋身體的第一套系統,而是第二套。我在醫學院裡學到的是化約式的現代醫學,在那套醫學之前,西方原本還有另一套不同的醫學系統。那套「前現代醫學」源自於西元前五世紀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人們曾經依據那套系統來理解人體。我研讀希德格的醫學時,發現那套系統採用的不是機械論。換言之,他們並非把身體想像成機器,疾病也不是機器發生故障。
不過我也很想知道,在我接受醫學教育的兩千五百年前,如果當時人們不是把身體想像成機器,那麼又是如何想像的?西方醫學界對於遺體和生命體之間的差異,以及對於我在行醫時的其他體驗,是否有過相對應的解釋?那些解釋是否都因現代醫學占了上風而遭到淘汰?前現代醫學和現代醫學會不會是一體的兩面?它們會不會是分別從兩個角度來看待人體,就像可同時看出兩種不同圖像的圖畫一樣?
我不知道,但十分好奇,決定一探究竟。
因此我需要時間,偏偏時間也是現代醫學認為落伍的概念。在前現代時期,醫學不是全職的專業,而是傳家的技藝,師徒代代相傳,因此,大多數行醫者不只是醫生,也身兼其他工作。其中的精英是醫生兼教授,大多數則是醫生兼務農,醫生兼藥草師,醫生兼理髮師。這樣有些好處。對病患來說,這表示醫生看事情的角度不只一種;對醫生來說,這表示他有時間以其他方式來思考其他的事。
到了現代,醫學訓練既辛苦又昂貴。從專業和財務角度來看,醫生有義務不分晝夜、時時刻刻堅守崗位,為病患待命。他們幾乎沒有私人時間,兼職的醫療工作更是聞所未聞。如今,情況又不同了,醫學已完全蛻變,從技藝轉變為專業,再轉變為商品,當前的醫療照護者在公開市場上分段販售他們的商品—─他們的時間。回想當年,我想找一份能讓我兼顧行醫並攻讀醫學史博士學位的工作,找了好幾個月都未能如願。
有農場的醫院
後來,我與舊金山深池醫院的醫療主任梅潔醫師聯絡,梅潔醫師在電話上向我保證,她可以配合我的兼職要求。她說,她聘用的多位醫生平時也做其他的事,有人是醫師音樂家、醫師雕刻家、醫師物理學家,也有人身兼母職。她知道彈性時間是她必須提供的特殊福利。
於是我開車過去面試,心裡有些存疑。
第一眼看到深池醫院時我大吃一驚。我在接受醫療訓練時,偶爾會將病患轉到這裡來休養,但我和舊金山大多數醫生一樣,從沒來過這裡。要是有人問我,我會說,想像中這是一棟類似停車大樓的混凝土結構建築,坐落在市內陳舊的工業區某處,病患分別待在一層又一層的樓層裡。然而並不。當我開車進入大門,經過廢棄的警衛室時,看見的卻是一棟雅緻但低調的仿十二世紀羅馬式修道院。醫院位於山丘上,是紅頂的桃色建築,可俯瞰海洋;六棟側翼建築全都有一排排的窗戶,每棟的盡頭各有一座角樓,燕子從開放的拱門飛進飛出。
我到梅潔醫師的辦公室和她碰面。面試結束後,她帶我參觀醫院。她開始導覽前先向我解釋,深池醫院原本是救濟院,法國人稱為神恩院舍(Hôtel-Dieu),是一種源自中世紀的醫療院所,目的是照護無法照顧自己的人。她說,過去有一段時間,美國幾乎每個縣內都有一間救濟院及一間縣立醫院,兩者相輔相成。理論上,縣立醫院負責照護重症患者,救濟院照護長期的身心不便病患。不過在實務上,救濟院接受其他地方無法收留的所有人。它就像庇護所、失業棲身處、中途之家、復健中心,也是醫院。不過,在過去四十年間,除了深池醫院外,美國幾乎關閉了所有的救濟院。梅潔醫師說,深池醫院可能是美國碩果僅存的救濟院3,院內共有一千一百七十八位患者,就像一個大村落。
我們經過舊金山守護神聖方濟的細緻木質雕像,進入寬敞的中央大廳,裡面有從天花板延伸到地板的落地窗,還有自動販賣機和小圓桌,廳內坐滿了抽菸、喝咖啡、打牌的患者。接著,我們轉身推開幾道厚重的大門,進入病房區,沿途經過小型的開放式廚房、用餐區、醫師辦公室、護理站,然後來到又深又長的開放式病房。
病房裡有成排的病床,每側各十五床。每張床都位於打開的窗戶旁邊,床邊都有收納病患私物的小櫃子、一張為訪客準備的椅子,還有一張小桌子。病房盡頭是一個明亮通風的圓型房間,那是做日光浴的地方,這樣病患不必離開病房就能享受陽光和新鮮的空氣。(原來那就是角樓的用途!)梅潔醫師解釋,醫院裡共有三十八個病房,每個病房大致都差不多。這是在抗生素發明前設計的建築,因此,萬一出現感染病例,每個病房即使和醫院的其他部分隔離,仍可像獨立的小醫院般繼續運作。
之後我們漫步往回走,穿過那個有自動販賣機和病患聚集的大廳,經過一間一九五○年代風格的美容院,裡面還有鋼盔狀的吹風設備,以及鋪著人造皮革的旋轉椅。我們還往理髮院探看了一下,裡面有個迷你型的旋轉式理髮店招。我們接著上樓去看手術室和化驗室。手術室鋪著青瓷色的瓷磚,放了幾個玻璃櫃,化驗室裡有黑色的實驗台、顯微鏡、離心分離器。梅潔醫師也帶我去看賣糖果、電池、刮鬍膏的小店,還有有一排排藏書的圖書館,館內有橡木桌,木架上擺著報紙。
我們往下走了幾層,來到戲院。這裡的水泥地板塗了油漆,擦得光亮。舞台上垂著紅色的天鵝絨布幔,我們身後是有雕刻圖案的包廂座椅。梅潔醫師說,以前這戲院曾用來放映默劇,由院長的兒子負責手搖影片,現在主要用來舉辦耶誕節的表演,以及情人節的舞會。戲院旁邊是禮拜堂,那裡不像現代醫院裡冷清的「安靜房」(Quiet Room),比較像小教堂,彩色的玻璃窗寬大而真實,教堂長椅以拋光的木材製成,牆上掛著一排十四幅耶穌受難像。
隨後梅潔醫師帶我走到室外。
她告訴我,深池醫院占地六十二英畝。這裡原本不只是醫院,也是農場。他們期望患者有體力能勞動時就參與工作,種植醫院使用的多數蔬果,照顧酪農場,餵養豬隻和牛羊,清洗與縫補衣服,料理食材,如果做不來,可以負責園藝。走著走著,我看到舊的果園和花圃的遺址,如今都已雜草蔓生。那裡有蘋果樹、柑橘樹、橄欖樹和無花果樹,樹木之間散布著藥草,有洋地黃、迷迭香、金蓮花、薰衣草、天竺葵、纈草。最後,我們來到院區導覽的終點站—溫室、鳥園和穀倉前院。
溫室散發著腐質土和植物的味道。梅潔醫師解釋,每個星期六,治療師會帶病患出來,讓他們坐在木製長椅上栽種植物。溫室旁是鳥園,裡面有鴿子、鸚鵡、雞和孵蛋器。後來我發現連愛滋病房都有一套孵蛋器,他們在病房裡孵育小雞。那隻雞就在病房裡走來走去,在病床邊啄食,直到州政府發現後才把牠帶走,沒有人知道牠後來的命運。
我們最後看了一下穀倉前院。右邊是兔子的木籠,左邊是雞籠,中間是自由活動的綠地,還有兩隻黑色的迷你豬。後方矮籬外有一個養鴨、鵝的池塘,還有一個有隻火雞和兩隻山羊棲息的小土丘。梅潔醫師告訴我,在某些節日,治療師會把這些動物放上小推車,推去造訪臥床的病患。他們會幫動物穿上合適的節慶裝扮,如感恩節時,山羊戴著清教徒小帽,美國國慶時,火雞戴上墨鏡,繫著領帶。
接著我們走回她的辦公室,坐下來。那間辦公室很樸實,有張大桌子,書架上放著報告與手冊,窗子面對停車場,可以看到救護車來來去去。
梅潔醫師當下就錄用我了。
反倒是我自己沒那麼肯定。深池醫院和我見過或想像的醫院不一樣,但那裡是唯一能滿足我時間安排的地方。於是我接下了那份工作,不過只是暫時接受。我告訴她,我只會待兩個月,我只能先承諾工作兩個月。我那麼做只是想為自己留條退路。我覺得她應該不會接受,畢竟為了那兩個月的工作幫我辦理雇用手續,實在太麻煩了。
不過梅潔醫師顯然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深池醫院有某種吸引力。幾乎所有人本來都只打算待幾個月,或者一、兩年,但後來大多數都是一待數十年—三、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她兩年半前剛來時,原本只是來提供四週諮詢的。
海潔醫師很肯定我也會臣服於那股吸引力。
她說的沒錯,我確實深受吸引。
我不只在深池醫院待了兩個月,而是二十多年。那段期間,我研究希德格的醫學,完成了博士學位;我展開一段中世紀的朝聖之旅後又回來。這座古老的救濟院轉變成現代化的醫療照護設施時(無論那是好是壞),我也在場。總之,我在這裡照顧了一千六百八十六位患者,他們教了我許多事,改變了我,也以始料未及的方式改變了我的醫療觀。
梅潔醫師答應我暫待兩個月的要求。我大感意外。
她告訴我,我的工作內容是到入院病房區接手賈德醫師的工作,賈德醫師則會轉調到其他病房服務。我三個星期後開始上班。上班第一天,我必須先到人事部門簽署相關文件,然後到洗衣房領一件白袍,再到入院病房區和賈德醫師碰面。他會帶我認識環境,把他的病人交接給我。